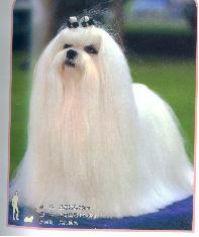(这篇博客已归入新浪博客)
为母亲节献上一篇多年前的文字!

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,母 亲 节 时,难 免又 回 想起 我的 母 亲,以及母 亲 的 母 亲 - 姥 姥。
母 亲 出 生 在 河 北 省 平 山 县 的 一 个 小 山 村 - 东 冶 。 尽 管东 冶 村 依 山 傍 水,山 清 水 秀。 可 在 20 年 代, 这 个 偏 僻 山 村 大 多 数 农 民 的 生 活 却 是十 分 贫 苦。 如 果 单 靠 姥 爷 租 种 的 几 亩 薄 田, 五 口 之 家( 母 亲 有 两 个 弟 弟〕 也 很 难 度 日。 但 姥 姥 有 一 双 远 近 闻 名的巧 手。 她 为 方 圆 几 十 里 的 人 家 缝 制 服 饰, 嫁 装,寿 衣 等,日 子 虽 然 清 苦, 但 不 至 于 愁 吃 愁 穿。
姥 姥 没 有 读 过 一 天 书, 可 她 好 像 通 古 博 今, 肚 里有 着 说 不 完 的 故 事。她 不 仅 会 描 龙 绣 凤,缝 制 象 古 装 戏 里 人 们 穿 的 五 光 十 色 的 服 饰, 而 且 她 绣 在 衣 服 上 的 花 草 人 物, 往 往 都 和 一 些 传 说,典 故 有 关。 目 不 识 丁 的 姥 姥 还 会 针 灸! 给 乡 邻 针 灸 姥 姥 从 来 不 取 报 酬。 听 说也 有 不 少 周 围 村 落 的 人 们 翻 山 越 岭 来 找 姥 姥 看 病 的。在 当 时 那 个 小 小 的 山 村 里, 姥 姥 自 然 成 为 村 里 大 人 孩 子 最 待 见 的 人。
我 始 终 不 太 明 白 姥 姥 是 从 哪 儿 学 会 针 灸 的。 好 像 母 亲 说 过 是 跟 姥 姥 的 父 亲 学 的。 但 记 不 太 清 楚 了。 我 只 知 姥 姥 出 生 在 一 个 很 大 的 家 庭。 兄 弟 姐 妹 很 多,我 至 今 还 保 留 着 一 张 解 放 以 后 姥 姥 七 个 姐 妹 一 起 照 的 照 片。 这 张 照 片 曾 给 我 许 多 联 想, 这 里 不 知 蕴 藏 着 多 少 动 人 的 关 于 母 亲 们 的 故 事。 真 希 望 有 机 会 寻 根 探 访, 多 多 了 解 我 们 前 辈 的 那 些 母 亲 们。
妈 妈 不 仅 长 得 象 姥 姥, 性 格 也 十 分 相 象。 两 道 弯 眉 下,也 有 着 一 双 秀 目。 温 顺 中 透 出 倔 强。 从 小 聪 敏 伶 俐, 好 学 要 强。 7, 8 岁 时, 就 懂 事 达 理, 拣 柴 烧 火,带 两 个 弟 弟,成 了 姥 爷 姥 姥 的 好 帮 手。 他 们 对 母 亲 也 格 外 疼 爱。
当 时 的 女 孩 子 都 裹 脚。 小 脚 是 找 婆 家 的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先 决 条 件。 婆 家 挑 人,首 先 看 脚,有 时 比 长 相 还 重 要。 女 孩 子 从 五, 六 岁 起,一 直 到 十 三, 四 岁,每 天 裹 脚 时 都 疼 痛 不 堪, 直 到 脚 定 了 型。 姥 姥 的 脚 裹 的 很 小, 可 谓 标 准 的 三 寸金 莲。 老 年 的 姥 姥 体 态 微 胖, 我 们 都 能 体 会 小 脚 给 她 一 生 带 来 的 痛 苦 和 不 便,母 亲 四,五 岁 时 , 姥 姥 也 开 始 给 她 裹 脚, 每 次 裹 脚 时,看 着 女 儿 秀 丽 脸 上 疼 痛 的 表 情, 姥 姥 心 疼 不 己。 到 女 儿 六,七 岁 时, 姥 姥 作 出 了 一 个 让 全 村 人 吃惊 的 决 定。 把 母 亲 的 脚 放 开 了。 村 里 好 心 人 都 劝 姥 姥, 姥 爷,怕 女 孩 子 以 后 不 好 找 婆 家。 其 实 这 事 儿, 姥 爷 姥 姥 已 商 量 多 时, 最 后 可 能 还 是 姥 姥 说 服 了 姥 爷 。作 出 了 这 个 在 当 时 颇 为 大 胆 的 决 定。 姥 爷 是 村 里 有 名 的 老 实 人, 性 格 开 朗,又 好 帮 助 人,在 村 里 人 缘 很 好, 但 比 较 胆 小,象 这 样 的 大 事 多 半 是 姥 姥 作 的 主。
当 时 中 国 新 文 化 运 动 正 在 兴 起, 只 有 在 一 些 大 城 市,开 明,进 步 的 妇 女 才 开 始 放 脚。 在 那 个 小 小 的 北 方 山 村 , 一 个 没 有 文 化 的 普 通 农 村 妇 女 的 这 一 举 动, 在 当 时 肯 定 没 有 多 少 人 能 理 解。 我 想 这 一 方 面 是 因 为 姥 姥 对 女 儿 的 疼 爱, 另 一 方 面 是 姥 姥 与 众 不 同 的 见 识 和 勇 气。 后 者 使 她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作 出 了 一 些 惊 人 的 决 定。
在 母 亲 十 一, 二 岁 的 时 候, 省 吃 俭 用 的 姥 爷, 姥 姥 把 母 亲 送 进 了 邻 村 的 学 堂。当 时 大 舅 已 经 七,八 岁,也 是 上 学 年 龄, 但 家 境 只 允 许 一 个 孩 子 上 学。在 这 种 情 况 下,即 便 是 较 富 裕 的农 村 家 庭, 一 般 也 只 送 儿 子 上 学, 决 不 会 象 姥 爷,姥 姥 那 样, 让 母 亲 先 进 了 学 堂。 我 们 知 道,在 21 世 纪 今 日 的 中 国, 还 有 少 数 落 后 地 区 的 农 村,在 那 里,学 习 依 然 只 是 一 些 男 孩 子 们 的 权 力 。 因 为 姥 姥 超 前 的 明 智, 母 亲 的 一 生 因 此 而 奠 定 了 一 个 坚 实 的 基 础。
聪 颖 好 强 的 母 亲, 一 旦 有 了 学 习 机 会, 格 外 珍 惜, 在 短 短 3 年 时 间 里 读 到 了高 小(5 年 级), 成 绩 极 为 优 秀。 所 以 当 县 里 一 个 开 明 人 士 创 办 了 第 一 所 女 子 师 范 专 科 学 校 时, 母 亲 被 保 送 进 了 师 专。 经 过 一 年 多 的 学 习, 母 亲 各 方 面 进 步 很 快, 因 为 她 豪 爽, 侠 义 的 性 格, 在 学 校 里 结 交 了 许 多 朋 友, 初 步 显 示 了 她 卓 越 的 领 导 和 组 织 能 力。 当 县 里 一 所 新 开 的 中 学 急 需 女 教 师 时, 学 校 允 许 母 亲 提 前 毕 业, 当 时 只 有 16, 7 岁 的 母 亲 成 了 可能是平 山 县 有 史 以 来 的第 一 位 中 学 女 教 师。
记 得 母 亲 曾 给 我 们 讲 过 一 个 有 趣 的 故 事: 到 学 校 不 久, 一 位 学 生 家 长(是 当 地 的 有 名 的军 阀,为 显 示 其 开 明 进 步,捐 了 一 笔 钱 给 学 校, 校 方为 此 组 织 了 一次 操 练 活 动, 请 那 位 军 阀 检 阅。 每 个 班 的 教 员站 在 自 己 班 的 学 生 前 面 领 队。
操 练 开 始 之 前, 军 阀 突 然 指 着 站 在 学 生 前 面 领 队 的 母 亲 问:“ 那 个 小 丫 头 片 子 站 在 那 儿 干 啥?” 听 说 母 亲 是 教 员 后,那 个 军 阀很 不 以 为 然, 校 方 真 有 些 担 心,怕 因 此 会 影 响 这 次 捐 款。 但 母 亲 带 的 班 在 检 阅 中 表 现 突 出, 军 阀 十 分 满 意。 在 此 之 后 居 然 提 出 要 母 亲 做 他 女 儿 的 家 庭 教 师, 让 母 亲 搬 到 他 家 里 去 住,母 亲 当 然 没 有 同 意。 这 个 军 阀 后 来 还 曾 纠 缠 不 休, 但 第 二 年, 当 母 亲 18 岁 时, 在 姥 爷 姥 姥 的 支 持 下, 她 参 加 了 革 命, 投 身 于 艰 苦 而 伟 大 的 八 年 抗 日 战 争 中。
最 为 让 我 敬 佩 的 是 在 两 个 舅 舅 刚 成 年 之 后, 姥 姥, 姥 爷 把 他 俩 也 相 继 送 入 革 命 队 伍, 追 随 母 亲,开 始 了 他 们 革 命 的 生 涯。 在 那 出 生 入 死 的 艰 苦 战 争 岁 月, 作 为一 个 母 亲, 需 要 多 么 大 的 勇 气, 多 么 宽 阔 的 胸 怀 才 能 为 了 民 族 的 解放 将 其 所 有 子 女 都 送 上 前 线! 姥 姥 自 己 在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也 曾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掩 护 过 受 伤 的 八 路 军, 还 曾 将 自 己 家 里 的 最 后 一 点 口 粮 送 给 了抗 日游 击 队。
小 时候, 我 们 经 常 要 求母 亲 和 姥 姥 给 我 们 讲 她 们 在 抗 日 战 争 和 解 放 战 争 期 间 的 一 些 经 历, 对 我 们 来 讲 那 都 是 一 些 十 分 惊 险 或 有 趣 的 故 事, 这 些 故 事 中 姥 姥 和 妈 妈 显 示 了 她 们 特 有 的 那 种 仗 义, 豪 爽 的 性 格。 这 些 常 常 使 我 联 想 起 武 侠 小 说 中 那 些 伸 张 正 义, 劫 富 济 贫 的 女中 豪 杰。
无 论 是 在 战 争 年 代, 还 是 在 和 平 时 期, 她 们 始 终 保 持 着 她 们 的 这 种 热 情, 正 义 和 纯 朴。许 多 跟 她 们 相 处 过 的 人 都 为 她 们 的 性 格 所 感 染。 作 为 晚 辈, 我 也 有 许 多 这 方 面 的 亲 身 经 历。
我 是 在 解 放 前 夕 的 一 个 严 冬, 出 生 在 承 德 山 区 的 一 个 小 山 沟 里。 那 时 父 母 转 战晋察冀 , 战 情 十 分 紧 迫, 出 生 第 二 天, 母 亲 坐 着 担 架 出 发, 时 值 腊 月, 山 区 寒 风 刺 骨, 警 卫 员 把 我 用 棉 被 裹 好, 放 在 一 个 小 竹 筐 里,盖 得 严 严 实 实, 背 在 背 上。 行 军 路 上,不 时 掀 开 棉 被 查 看 怕 出 什 么 意 外。 几 天 后, 为了全 力 以 赴 投 入 战 斗,父 母 把 我 寄 养 在 当 地 一 贫 苦 农 家, 他 们 后 来 就 成 了 我 的 干 爹 和 干 娘。 干 娘 的 儿 子 刚 刚 断 奶, 他 们 两 口 子 待 我 象 亲 生 女 儿 一 样, 父 母 很 感 激 他 们 的 帮 助, 解 放 以 后 曾 多 次 赶 到 山 区 看 望 他 们, 三 年 困 难 时 期,母 亲 还 为 他 们 寄 过 钱 和 粮 票。
两 三 岁 时, 因 父 母 南 下,把 我 和 妹 妹 留 在 了平 山 老 家。 小 时 候 我 们 十 分 乖 巧。 姥 姥 非 常 疼 我 们, 经 常 给 我 们 做 漂 亮 的 衣 服 和 鞋 帽, 鞋 上 通 常 都 绣 着 花。 我 还 隐 隐 约 约 记 得 小 时 候 穿 上 新 衣, 新 鞋 以 后 的 得 意。 后 来 随 父 母 从 安 徽 到上 海, 又 从 上 海 到 天 津, 直 到 上 中 学, 姥 姥 还 经 常 给 我 们 做 鞋 寄 来, 有 时 还 绣 上 花。稍 大 后, 就 不 再 敢 穿 这 样 的 鞋 上 学 了, 但 每 当 收 到 鞋 后 总 是 格 外 想 念 姥 姥,想 起 她 的 关 怀 和 慈 祥,所 以 即 便 不 穿,也 会 把 新 鞋 包 好,小 心 的 收 藏 起 来。
困 难 时 期, 姥 爷 因 营 养 不 良 病 逝, 母 亲 把 姥 姥 接 到 天 津。 有 一 段 时 间, 父 母 在 南 方, 姥 姥 和 我 们 姐 妹 几 人 留 在 天 津。 我 们 当 时 都 住 校, 每 周 日 才回 家。 姥 姥 总 是 把 好 吃 的,有营 养 的 东 西 省 下 来 给 我 们 吃, 现 在 想 起 来, 姥 姥 自 己 可 能 当 时 经 常 吃 不 饱, 因 为 配 给 的 食 物 是 极 其 有 限 的。 至 今 还 记 得 周 末 回 家 姥 姥 常 给 我 们 做 辣 椒,胡 萝卜 炒土 豆。 菜 炒 得 很 香, 可 能 把 一 个 星 期 的 油 都 用 上 了。 那 时 虽 然 学 生 有 特 殊 补 贴,但 定 量 不 够, 也 得 糠 菜 充 饥。 学 校 的 伙 食 油 水 更 是 少 的 可 怜, 正 在 长 身 体 的 我 们 常 常 感 到 饥 饿。 所 以 周 日 的 “ 开 斋” 是 我 们 最 开 心 的 时 刻。 后 来 我 也 多 次 试 着 炒 同 样 的 菜,但 再 也 吃 不 出 姥 姥 炒 的 菜 的 那 种 香 辣 的滋 味。
姥 姥 不 仅 省 吃 俭 用 照 顾 我 们, 而 且 还 经 常 无 私 地 帮 助 他 人 。 记 得 有 一 次, 司 机 的 爱 人 带 孩 子 来 津 看 病。手 头 很 紧, 姥 姥 不 但 把 自 己 身 上 所 有的 钱 都 给 了 他 们, 而 且 在 他 们 临 走 时, 姥 姥 还 给 那 个 孩 子 做 了 好 几 件 衣 服 带 上。姥 姥 的 同 情 心 和 助 人 为 乐, 对 我 们 影 响 也 很 大。 我 们 也 都 很 体 贴 姥 姥。 记 得 学 校 有 一 次 发 柿 子 给 我 们, 我 不 知 从 哪 里 听 说 柿 子 对 咳 嗽 有 好 处, 想 起 抽 烟 的 姥 姥 经 常 咳 嗽, 我 就 小 心 翼 翼 把 柿 子 藏 起 来, 等 到 周 六 回 家 时, 装 在 书 包 里,兴 冲 冲 地 跑 回 家 想 带 给 姥 姥 吃, 路 上一 不 小 心, 摔 了 一 个 跟 头, 放 了很 长 时 间 的 柿 子 软 得 很, 破 了 后, 弄 得 满 书 包 都 是。
每 当 回 忆 起 姥 姥 时, 总 是 想 起 在 天 津 的 那 段 经 历。 想 起 晚 上 关 灯 后,与 我 们 姐 妹 几 人 住 在 同 一 房 间 的 姥 姥, 盘 腿 坐 在 床 上,抽 着 烟 斗, 给 我 们 讲 一 个 个 有 趣 的 故 事, 直 到 我 们 入 睡。 姥 姥 烟 斗 在 黑 暗 中 那 一 闪 一 灭 的 火 光 一 直 深 深 地 留 在 我 的 记 忆 中。
母 亲 的 性 格 和 姥 姥 有 很 多相 似 之 处。解 放 以 后,尽 管 她 曾 历 任 安 徽,上 海 和 河 北 省 政 府 机 关 要 职。 但 对 同 事,下 级 的 真 诚 和 宽 宏 大 量, 象 在 战 争 时 期 一 样, 为 她 赢 得 了 许 多 真 正 的 朋 友。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这 样 的 政 治 运 动 中,母 亲 也 因 她 的 直 率 和 主 持 正 义 受 到 了 残 酷 的 迫 害 和 打 击。可 就 是在 那 些 最 艰 难 的 时 候,她 还 始 终保 持 着 她 的 乐 观 与 大 度。
文 革 初 期, 母 亲 和 许 多 老 干 部 被关 进 了 设 在 保 定 市 省 委 大 院 里 的 “ 牛 棚”, 遭 到 了 非 人 的 待 遇。 不 少 老 干 部 被 打 致 残, 还 有 一 些 人 忍 受 不 了残 酷 的 折 磨 自 杀 身 亡。 当 得 知一 个 中 学 同 学 的 父 亲 在 那 里 自 杀 的 消 息 后,我 们 分 外 焦 虑。加 上 我 们 姐 弟 几 人 将 相 继 上 山下乡,所 以 我 和 一 位 父 亲 也 被 关 在 同 一 处 的 同 学 立 即 从 天 津 赶 往 保 定 希 望 能 在 下乡以 前 见 一 见 母 亲, 但 去 了 多 次,均 被 把 守 的 造 反 派 拒 绝。 最 后 只 好 托 我 们 家 老 保 姆 在 保定 当 工 人 的儿 子-金 壮,把 一 封 信 设 法 转交 给 了母 亲。我 们 怀 着 极 其 担 忧 的 心 情 告 别 了 年 老 体 弱, 将 被 送 往 干 校 的 父 亲, 离 开 了 天 津, 奔 赴 内 蒙, 山 西 等 地 农 村。
记 得 当 我 接 到 第 一 封 来 自 保 定 的 书 信 时,看 着 被 拆 开 过 的 似 乎 沾 有 血 迹 的 信 封 时,担 心 万 分。 但 信 的 内 容 却 使 我 非 常 惊 讶。 我 记 得 很 清 楚,母 亲 以 轻 松 乐 观 的 语 调 告 诉 我 她 那 里 一 切 都 很 好, 让 我 们 放 心, 还 用 了 很 大的 篇 幅 开 导 我 们,在 艰 苦 的 时 刻 要 有 乐 观 的 精 神,要 能 上 能 下,珍 惜 在 农 村 的大 好 机 会,锻 炼 提 高 自 己,相 信 我 们 的 一 生 将 会 因 此 而 受 益 不 尽……
读 了 信,敬 佩 和心 痛,百 感 交 加。敬 佩 的 是:母 亲 在 遭 受 着 如 此 大 的 精 神 和 肉 体 上 的 折 磨 时,还 那 么 豁 达,开 朗, 考 虑 到 的 只 是 我 们 的 成 长 和 前 途。 心 痛 的 是:为 革 命 出 生 入 死, 忠 心 耿 耿,奋 斗 了30 多 年 的 母 亲,至 今 却 遭 受 到 如 此 不 公 正 的 待 遇 和 折 磨! 我 们 诸 多 儿 女,远 隔 千 里,无 能 为 力。当 我 把 信 给 我 同 一 集 体 户 的 一 个 好 朋 友 看 后, 在 那 个 冰 天 雪 地 内 蒙 古 的 一 间 土 屋 里,在 那 盏 昏 暗 的 油 灯 下,我 们 两 人 流 着 泪, 暗 下 誓 言, 一 定 要 争 这 口 气, 为 我 们 的 前 辈, 也 为 我 们 自 己……
后 来 情 况 稍 有 好 转, 母 亲 被 送 到 了 河 北 的 一 个 干 校 “接 受 再 教 育“。 我 和 妹 妹 有 机 会 同 去 探 视。 当 分 别 两 年 的 母 女 相 见 时,原 本 满 头 乌 发 的 母 亲 已 是 两 鬓 斑 白。 农 村 生 活 的 磨 炼 也 使 文 弱 的 我 们 变 的 面 孔 红 黑,身 体 强 壮。 当 干 校 的 叔 叔 阿 姨 夸 奖 我 们 时,母 亲 的欣 慰 和 自 豪 自 然 是 不 言 而 喻。 记 得 妈 妈 拉 着 我 的 双手 对 同 屋 的 阿 姨 说:” 她 原 来 这 双 手 纤 细 白 嫩, 现 在 比 以 前 粗 壮 多 了, 这 就 是 上 山 下 乡 的 收 获“。 这 时,我 注 意 到 母 亲 的 左 手 有 些 变 形,问 她 时,母 亲 轻 描 淡 写 的 说 可 能 是 因 为 风 湿 性 关 节 炎 引 起 的。 后 来,还 是 从 那 位 忠 心 耿 耿,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间 一 直 设 法 照 顾, 保 护 我 们 的 老 保 姆 那 里 得 知 实 情。 老 保 姆 的 儿 子 金 壮, 为 人 正 直,在 工 人 中 很 有 威 信, 他 出 生 又 好,所 以 是 他 们 工 厂一 派 组 织 的 头。 他 知 道 母 亲 关 在 保 定, 所 以 想 方 设 法 探 听 有 关 母 亲 的 消 息。 千方百 计 出 面 干 涉, 保 护 母 亲。 在 每 一 次” 批 判 “母 亲 的 公 开 场 合, 只 要 可 能 他 总 是 设 法介 入,尽 量 靠 近 母 亲 站 着, 以 防 万 一。 在 这 样 的 一 次 ” 批 斗 会“上,一 个 以 前 被 母 亲 审 查, 处 理 过 的 所 谓 “造 反 派” 冲 到 台 上,手 持 铁 棍, 冲 着母 亲 的 头 部 打 去。 母 亲 抬 起 左 手 挡 了 一 下, 虽 然 被 打 得 血 流 满 面, 但 头 部 伤 势 不 重,只 是 左 手 受 伤, 小 指 被 当 场打 断。 那 个 所 谓 造 反 派 举 起 棍 子 还 要 下 手, 被 站 在 旁 边 的 金 壮 推 到 台 下。
母 亲 从 来 不 跟 我 们 提 起 在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间 的 这 些 遭 遇,但 常 以 感 激 的 心 情 谈 到 文 革 期 间 那 些 真 正 的 朋 友 们。 因 为 父 母 的 宽 厚 和 平 易 待 人, 他 们和 一 些 普 通 老 百 姓, 和 他 们 的下 级 常 常 相 处 地 和一 家 人 一 样。 文 革 期 间,在 父 母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, 他 们 曾 冒 着 风 险, 前 来 探 望 父 母 。 其 中 有 战 争 时 期 跟 随 父 母 多 年 的马 夫,有 那 位 背 过 刚 出 生 我 的 警 卫 员, 有 解 放 后 他 们 的 秘 书 和 保 姆。 一 位 带 我 弟 弟 长 大 的 年 近 70 的 老 保 姆, 在 文 革 中, 不 远 千 里, 从 安 徽 赶 到 天 津 探 望 我 们。 她 说 在 安 徽 时 听 到 许 多 传 闻, 他 们 全 家 很 不 放 心。 因 为 她 的 女 儿 和 女 婿〔父 亲 原 来 的 警 卫 员〕 都 去 了 干 校, 所 以 托 她 只 身 来 津 探 望, 希 望 父 母 要 想 得 开,多 多 保 重 等。 这 一 切 都 给 我 们 留 下 深 深 的 印 象。
文 革 后 的 母 亲 又 热 情 地 投 入 新 的工 作, 似 乎 希 望 以 加 倍 的 努 力 来 弥 补 失 去 的岁 月。 60 多 岁 的 母 亲 患 有 严 重 的 高 血 压, 超 负 荷 的 工 作 使 她 的 病 情 加 重,但 母 亲 从 来 也 没 有 一 天 停 止 过 工 作, 终 于 病 倒 在 工 作 岗 位 上。 在1983 年 患 脑 溢 血, 过 早 离 开 了 我 们。
多 年 来。 每 当 我 们 取 得 了 一 些 成 绩,总 会 想 起 母 亲 在 世 时 为 子 女 的 每 一 点 进 步 的 喜 悦。 记 得 母 亲 逝 世 前 几 个 月, 我 第 二 年 赴 澳 留 学 的 事 已 经 批 了 下 来,母 亲 得 知 后 十分 高 兴,曾 骄 傲 地 给 她 的 老 战 友 介 绍 说:”这 将 是 我 们 家 的 第 一 个 留 学 生,也 将 会 是 我 们 家 的 第 一 位 博 士“。 当 我 在 国 外 拿 到 学 位 时,我 是 多 么 希 望 能 和 母 亲 一 起 来 庆 祝, 多 么 想 再 看 一 看 母 亲 脸 上 洋 溢 的 那 种 满 意 和 自 豪。
身 在 异 国, 母 亲 节 时总 是 感 慨 万 分。对 姥 姥 和 母 亲 的 回 忆 使 我 时 时 想 写 些 什 么。 可 多 次 动 笔 后, 因 种 种 原 因,难 以 继 续。 这 次, 终于鼓 足 了 勇 气 ,拿 起 生 疏 的 笔, 试 着写 一 写 我 的 怀 念, 写 一 写 我 的 感 激。

















.JPG)

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










.JPG)


.JPG)
.JPG)
.JPG)
.JPG)

.JPG)
.JPG)
.JPG)